以下文章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作者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本刊的最新资讯和动态。

概念研究为什么重要?
——构筑教育学建设与发展的概念基石
李政涛1,2
1.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2.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
摘要:概念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通向“理论”。概念研究的重要性,来自于概念的重要性:“概念”是基础研究的根基或基石,“概念”演变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概念”潜藏了前提假设,“概念”体现了思维方式,“概念”包含了多元复杂关系。要更好地推动概念研究,需要更加关注思维方式、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融通转化、贡献能力和概念误区。
关键词:概念研究 ; 教育学 ; 思维方式 ; 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

李政涛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
目录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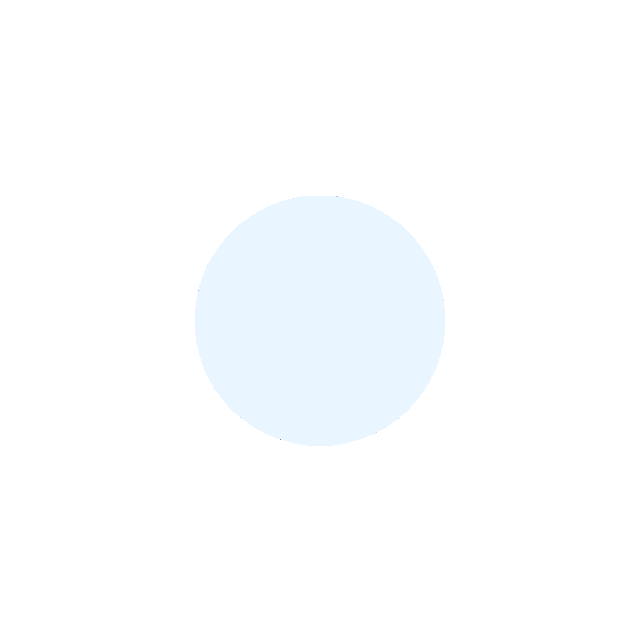
一、如何破除“概念研究”的成见?
二、为什么需要“概念”?
三、如何推动“概念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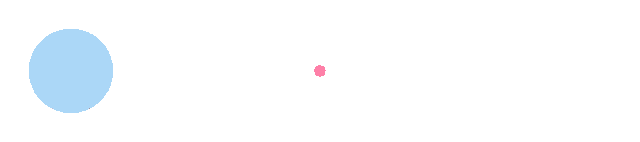
一、如何破除“概念研究”的成见?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言:“每一个人,无论去往何处,都会被一朵予人慰藉的信念之云围绕着,云朵随他而动,仿佛夏日的苍蝇”(索维尔,2023,扉页)。在理论的天空上,这朵信念之云,就是概念之云,它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概念研究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乃至被遗忘的问题。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对于教育学的原理性关切和概念性关切,是自身理所当然的使命与责任。在游历概念长河的历程中,笔者所秉持的对“教育基本概念”的重视、挖掘和凝练,背后赖以支撑的是“概念敏感”“概念意识”和“概念自觉”。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同感,与之相反,随处可见的却是“概念迟钝”“概念轻视”“概念无视”,以及骨子里的“概念冷漠”“概念排斥”或“概念拒斥”,极端者则走向“概念敌视”“概念仇视”,遇见概念绕着走,看到概念就有除之而后快的冲动……归根结底,在于久已成习的概念偏见和概念成见。
在众多偏见者眼中,概念研究有“三宗罪”:一是抽象,它枯燥、干涩,远离具体、鲜活、生动的细节,虽不至于“面目可憎”,但至少让人索然无味,所以敬而远之。二是空洞,由于抽象,所以笼统、空乏,悬在空中,空落落地不着边际,落不了地,最终沦为空谈。三是无用,这是抽象空洞带来的后果:停留在“概念层面”的言说、辨析,滞留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循环和空转,看似严谨、严密,但与实事无关,与现实无缘,与生活剥离,尤其是对问题的解决无益。总之,概念研究最根本的罪过,是它创造的世界,是书本、理论的世界,是高高在上、远离人间的世界。要理解概念研究的重要性,自然无法回避如上根植于偏见的“指控”,不得不展开“无罪辩护”。
概念研究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实质上预设了一个更具原点性、前提性的问题:概念为什么重要?概念之所以重要,在根本上,它通向“理论”。概念本身的特质,是理论特质,它所遵循的逻辑,是理论逻辑,而不是实践逻辑,也由此成为具有“理论感”、走向“理论化”的基本标尺之一。更重要的还在于,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正如无法想象没有实验基础的科学一样,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概念基石的理论。理论的重要,验证了概念的重要,反之亦然:概念的重要,也说明了理论的重要。概念与理论之间互为表里,相互印证。
所有对于理论价值的肯定与否定,都离不开对理论特性或者理论逻辑的认识。其中被作为概念“罪状”之一的“抽象”,是把握理论特质和理论价值的关键枢纽:理论是抽象出来的,无抽象,不理论,无理论,不抽象。抽象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是人类极其宝贵的素养与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万花筒般的世界,人类能够抽离出最核心、最根本、最精髓的东西,而概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抽象而来的概念,并不必然引发空洞,空洞不是概念天然的附属物,概念是否空洞,取决于概念的具体内涵、界定方式及其运用方式。如同教育生活中的“表演”一样,表演自身没有先天的价值烙印,不带有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一种表演(如课堂上的表演)是否有教育价值,取决于为什么表演、表演什么、如何表演和谁表演。至于“理论的无用”这一流布已久的观念,早已不值一驳,无需赘述(李政涛,2023)。
然而,“理论的有用”不能直接推导为“概念的有用”,对“应然的认知”也无法替代“实然的存在”。概念有多么重要,并不广为人知,反而陷入久被忽略和遮蔽的状态。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任何对某种存在“重要性”的阐发和辨明,都离不开人类的“需要”,这是所有学科、理论、知识和技术诞生的源头。对于学科发展而言,没有需要,就没有一个学科的诞生,没有持续的需要,就不会有一门学科持续的发展。理论的重要性,无非在于人类需要理论,离不开理论,概念的重要性,也莫过于此。
二、为什么需要“概念”?
人类为什么需要概念,且离不开概念?可以从如下维度加以探析。
第一,“概念”是基础研究的根基或基石。
1945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发表了《科学:无尽的前沿》,这本书被后世推崇为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是对美国成为科技强国做出巨大贡献的扛鼎之作。布什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主张:“基础研究会带来新知识,是所有实际知识应用的源头活水,一切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都建立于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之上”(布什,霍尔特,2021,第30页)。所谓基础研究,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在不考虑实际需求、实际目的情况下对基础知识的寻求。基础研究填补的是一口井,而这口井是所有实用知识的来源。他眼中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研究和创新过程的推动力量,因此,无论哪个时代,都始终需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新华社,2020)。
范内瓦•布什阐明了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的关系,讲清了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科学概念的关系,凸显了科学概念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新的科学概念,带来新的科学知识,催生新的科学理论。
这里的基础研究,涉及到基础学科、基础理论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文学、史学、哲学等一样,教育学也是基础学科,内设专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理论,有必要将概念研究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让自身的概念根基和概念基石扎实、坚实和厚实起来,并通过概念性运用、建构和创造等一系列概念性活动,实现理论创新与思想创新。
不论哪一门学科,概念都是最基本的理论方式。以概念的方式展开理论活动,具体表现为提出概念、阐释概念、分析概念、运用概念、改造概念、建构概念,进而创造概念的活动。以哲学为例,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其思想的创造性、独特性总是体现在其核心概念之中,如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墨子的“兼爱”、柏拉图的“理念”、胡塞尔的“现象”、海德格尔的“存在”、福柯的“权力”、牛顿的“第一定律”、霍金的“时间”等,各自构成了哲学家们思想的基础性原点和原点性基础,成为思想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概念原点”。
第二,“概念”演变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部学科演变史,就是一部概念史。学科发展始终离不开自身基本概念的演进与变迁。注重概念分析的哲学和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的发展亦如此。
例如,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物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四次革命:力学革命、电磁学革命、相对论革命、量子革命(钱旭红,2023,第48页)。每一次学科革命,都是从新概念的提出开始的。概念革命引发了理论革命、学科革命,因此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此动力的推动下,学科知识创生、学科理论创新中发生的诸多对话、质疑和辩驳,展现出学科发展必须经历的各种探究、探险或历险的过程,而概念性都贯穿其中。一部学科探险记或历险记,就是概念探险记或历险记。
概念探险的过程,充斥着概念改造、概念重构、概念颠覆和概念移植。
再以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量子力学为例,量子力学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个有关“量子”概念的演变发展史。诞生于1900年的量子概念,先后经历了普朗克(Max Planck)的能量单元、能量子,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光量子、光子,波尔(Niels Bohr)的量子跃迁和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的量子纠缠等。一次次的概念演变、概念否定和概念重构,一次次颠覆着对原有量子的概念认知,在扩充人类对量子认识疆域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量子力学从旧量子力学到新量子力学的迭代演进。可以说,没有量子概念的演变发展,就没有量子力学的持续更新。
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交互生成过程中,“概念移植”成为推动的主要路径。例如19世纪末,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门社会科学自称拥有科学合法性,因为它们分别使用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这两门学科之所以自称完全有资格成为公认“科学”家族的成员,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它们与业已接受的物理学和生物科学据说有一种总体的相似性,在概念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对应性,比如“能量”(对应于“效用”)或“细胞”(对应于“个人”或“家庭”等社会实体)。经济学甚至会自豪地列出在形式上与物理学方程相同的方程(科恩,2016,第3页)。虽然,概念移植往往首先以类比的方式进行,如把有机体中的细胞比作社会群体的成员,或者把淋巴和血液比作运河、河流、道路和铁路系统,可能它的文学意义大于科学意义,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理论话语方式的丰富与更新。
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同样离不开对于“人”“教育”“学校”“课程”“教学”“教师”“学生”“知识”“能力”和“素养”,以及“教育学”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理解方式、研究方式与表达方式的演进。例如,对“人”的理解与界定,既是教育的前提,也是教育学的基础。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等不同时代,都会展现出对于人和人性不同的洞察与解读,形成时代性的教育观和教育学观。这种不同有时是差异,有时是冲突,各种观念的冲突时常通过概念的冲突表达出来,这些冲突在助力理论更新的过程中,塑造了我们所亲历的时代,也必将塑造未来;有时则是颠覆,造成对整个教育体系的典范性重置(李政涛,2023b)。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对“什么是人”的理解,颠覆了传统的“人-神”“人-物”的比较参照系,转向于“人-机”的参照系。又如,有关“教育”“教育学”的概念,寻遍所有的教育史和教育学史,其演化历程,都离不开人们对于这两个基本概念的理解与厘定(李政涛,2020;李政涛,2022)。在相当程度上,无论是教育史,还是教育学史,都是概念史,都是有关教育和教育学等基本概念的发展史和研究史。
概念如同地图,指引我们穿过令人迷惑、盘根错节和复杂多变的理论与实践。概念所具有的地图功能,与其本身所天然具有的抽象性相连:概念对碎片化经验和认识的高度抽象,得以让人类的目光从那些细枝末节、支离破碎的信息海洋中抽离出来,直接指向通往目标的最核心、最关键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学科地图就是概念地图,通过概念地图的勾勒,能够找到指向学科地图的描绘、铺展和运用的密码。
第三,“概念”潜藏了前提假设。
通过抽象得到的“概念”,既是人类观念的一部分,更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一种观念,各种概念及其观念,以彼此连接的方式,一直在悄悄地构造着人类的思想与理论。在此过程中,任何有关世界的观念和思想,都天然潜藏着某种前提假设。典型代表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观,其背后遵循了一种人性假设——人是自私的,在此基础上,他建构出了一套经济学意义上的道德激励体系。而作为教育学基本概念的“教育”,它潜含的是人具有可塑性、可能性的假设,人由此才有“可教性”。没有这一基本假设,就没有教育,也没有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创建的“普通教育学”。同理,作为教育学基本概念的“教学”,在深层次指向于教与学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构成了一种假设性的观念:没有教和学的互动关联,就不是“教学”,只是“学习”。多年前开始流行的“教师实践知识”,这个概念的假设是“与教育研究者一样,作为教育实践者的教师,也有自己的知识,也是知识的创造者,只不过它是实践知识”,它暗指对一个传统假设的颠覆:只有教育理论研究者才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教育实践者不是,他们只是理论研究者创造的教育知识的运用者。这是将教育实践者视为操作者的知识假设的根源之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实践知识”概念的提出、解释与运用,既促进了教师教育实践的拓展与深化,也造成了教师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重构。
前述所言的量子理论,其背后则是“量子假设”的支撑,即微观粒子的运动具有不连续性。这迥异于传统的经典牛顿力学、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的电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假设,后者视野中的粒子运动属性都是连续性的。显而易见,量子力学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倾覆性,首先在于它提出了革命性的概念“量子”,进而通过概念背后的前提假设,推翻了一系列传统理论的“传统假设”,用新假设翻覆旧假设,因而诞生了一个新的学科,让物理学等学科旧貌换新颜。这就是概念创新的价值:有了新概念,就有了新假设,在颠覆旧概念、提出新假设的同时,也颠覆了旧理论,促成了理论和知识的换代更新。
再举一个社会科学的例子。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提出的“个人知识”这个概念的假设是“个人也可以有知识”,它打破了以往的“知识假设”:知识是公众普遍的确信,是共识,知识的特性必然是客观、普遍性的,知识一旦个人化,将会陷入主观臆断。但波兰尼提出的“个人知识”观,颠覆了这个知识假设,因而推翻了传统知识观——一个奠基于“个人”而不是“群体或集体”的新知识观卓然而立。
概念背后的假设,在生活中也无处不在。笔者曾经在一所学校参观,学校安排了一个活动,让我们去看学生创作的绘画、雕塑和手工艺品,并且让学生讲解员介绍。其中一位女生在介绍一个学生的手工作品时说:“这个作品的主人,虽然是一位‘男生’,但他却心灵手巧……”这句话清晰地展露出她对男生或男性的一个预设性判断:女生普遍心灵手巧,男生则相反,心不灵,手不巧……该假设当然是有问题的。很多厨师、很多外科医生、很多艺术家特别是雕塑家,不都是男性吗?
总而言之,概念里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假设,如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是唯一的,还是多元的?等等。再往深里挖,这些假设其实也是诸多世界观、人性观的概念性体现,这些都是根子上的东西。在教育实践世界里,有“同课异构”,即同一课程内容,可以有不同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方式;而在教育理论世界里,则有“同概异构”,即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内涵结构与界定方式,而“异”的实质或根底,就在于前提假设的差异或迥异。
第四,“概念”体现了思维方式。
概念与思维的关联,一向紧密无间,类似于“一母同胞”。德国法学的标志性人物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曾言:“由于所有的法学都是借助概念运作的,所以‘法学思维’和‘概念思维’是同义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法学都是概念法学”(耶林,2023,第36页)。
教育学思维与教育学概念思维的关系亦然。1994年,叶澜在开启并推进“新基础教育”研究进而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过程中,生成的许多新概念如“成事成人”“以身立学”“深度介入”“生命自觉”等(伍红林,侯怀银,2022),其背面既有价值观的支撑,还有思维方式的运行。如“成事成人”与“生命•实践”这两个概念,均对准关联思维、融通思维:事与人的关联,事与人的融通,以及“生命”与“实践”的关联,“生命”与“实践”的融通。
就自然科学而言,还是以量子力学为例,它贡献给世人的不只是一套概念体系,还是一套与概念体系相连的思维体系,典型代表如“波粒二象性”。它的提出,不仅是在观点或观念上与经典力学有鲜明差异,而且也揭示了全新的思维方式。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是分解式或分离式思维:将微观世界分解为波的世界和粒子的世界;是割裂式思维:将波与粒子割裂开来;是非此即彼式思维:要么是波,要么是粒子;是静态性、直线性的思维,因而是固定性、确定性、定域式的思维方式。而量子力学的量子思维,则是关联思维、叠加思维、整体思维、融通思维、动态思维或跃迁思维,以及离域式的思维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依托波粒二象性的概念,量子力学引发的物理学革命,是思维革命。
倘若借用量子力学的第一层内涵(光既是波,也是量子)所展现的话语方式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很多二元对立式、非此即彼式的问题,如概念还是观念、经验还是先验、一元还是多元、中国还是世界、解构还是建构、不变还是变化、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等,都能够作出量子思维式的解答:既是概念,也是观念;既是经验,也是先验;既是一元,也是多元;既是中国,也是世界;既是解构,也是建构;既是不变,也是变化;既是中体西用,也是西体中用,等等。它们之间彼此关联、叠加、融通,因而纠缠在一起,构成了多重层面、多重视角和多重意义上的“量子纠缠”,成为一个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对于传统的提问方式及其解答方式,量子思维式的解答方式具有革命性,它引发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思维革命,它始终与概念研究特别是新概念的研究彼此纠缠:新概念的研究,表面上产生了新的知识框架,而知识框架背后的则是思维框架。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仅离不开对自身概念框架、知识框架的反思,更离不开对思维框架及其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的反思。正如科学史学家柯瓦雷(Alexandre Koyre)所言:“人要转变和更迭的不仅是他的基本概念和属性,甚至是他的思维框架本身”(柯瓦雷,2016,第2页)。如果说,不同概念体系背后,是诸种知识体系、范式体系的差异与冲突,那么再往深里挖掘可以发现,不同知识体系、范式体系背后,是纷繁多样的思维体系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些绵绵不断的观念冲突和思维冲突,持续重构并推动着学科跃迁式发展。
第五,概念包含了多元复杂关系。
一个概念不止于概念本身,不是个体性、孤立式的存在,而是包含了多元复杂的关系。
以“教育”这个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为例。
首先,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人类实践的样式之一,与政治实践、经济实践等相比,教育有自身独特的实践逻辑。与此同时,任何教育也都蕴藏着某种理论,它常常以理念、观念(核心是价值观)或思想的方式来呈现,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离。我们不可想象脱离实践的教育,也难以想象没有理念支撑的教育。
其次,包含了主体之间的关系。概念的提出者是人,阐释者、运用者和建构者也是人。换言之,人是概念的主体,参与且主导了从概念的提出、发生、发展到应用的全过程,构成了复杂的多元关系。就如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将作者与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作为“审美事件”的参与者,从而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样,概念与其提出者、应用者之间也构成了一种“事件性关系”(巴赫金,1996,第342页)。在这一“事件性关系”中,“这些概念获得自身内涵并开始诉诸行动的过程,与提出这些概念并试图用这些概念概括或掌握对象的作者之间,构成了一个运动中的整体”(汪晖,2023,第11页)。然而,这里的关系整体,包容了多种形态的关系:可能是和谐、统一或一致的关系,也可能是对立、矛盾或冲突的关系。因为对于同一概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阐释、运用与建构的方式,产生不同的概念活动,因而必然出现差异化甚至冲突化的“参与关系”和“交往关系”。教育中的主体交往关系,同样是多元的存在。例如,在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系上,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性质,建构理想的两大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是理解教育内涵、把握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前提与基础:“教育中理论与实践关联的性质,从本质上看是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都与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人相关……我们应该把研究的重心集中到更为根本的主体身上”(叶澜,2001)。
此外,还有多元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生成了教育的文化属性,而教育学与文化的关系同样牢不可破,相应地,也必然存在中国式教育或中国特色教育,其底蕴之一就是“文化式”“文化特色式”。与自然科学不同,教育学具有特殊的文化性格(石中英,2005)。因此,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教育学和德国教育学之间的关系,是两大文化主体即中国教育学人与德国教育学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主体间关系。
再次,包含了时空关系。概念具有时空性,存在“概念时间化”与“概念空间化”两种基本形态。在相当程度上,时间与空间也是概念产生和构建的源头,由此出现了来自时间的概念和源自空间的概念。当我们厘定教育的内涵之时,总是离不开时间的限定,对其展开历史性或者历时性的探索,因而出现了教育史研究的需要;亦总归离不开空间的限定,人类教育的多元景观,与区域或场域空间中的多样性有关,为此产生了“国际比较教育”的需要。
与此同时,概念的时间之维和空间之维,不是截然分离的。有学者以“区域”研究为例,发现形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的区域研究,呈现为两个主要特征:一个方面是空间时间化,另一个方面是时间空间化:“在目的论的时间性框架下,‘区域’这个空间概念被时间化,不同的区域从属于欧洲中心的或者日耳曼中心的历史叙述”(汪晖,2023,第7页)。在空间时间化的同时,也存在时间空间化现象。例如,“现代化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时间空间化,却在单线的时间框架下,按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等等一系列区划在空间上规划南北关系,在地域政治框架下规划东西关系,让这一空间划分服从于现代化的基础性的叙述” (汪晖,2023,第8页)。古往今来的“教育”概念,同样持续经历类似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的概念演变过程,因而不断重塑和再造教育的样态。
此外,包含了跨学科关系。概念及概念研究本来就是跨学科的,无论是“教育”,还是“人”“文化”“美”等,这些复杂的概念,都无法通过单一学科来独立思考和解决。每个概念,都是一种跨学科对话、借鉴、整合、交融与合作的可能和机遇。跨学科的对话和借鉴,往往从概念迁移、概念借用或概念类比、概念隐喻开始,如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首脑”概念,来自生理学。当我们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或者概念是学科理论的“细胞”时,这显然是对生物学“细胞”概念的类比或隐喻。进而言之,跨学科研究起步于概念研究。例如,相关学科要进入现象学的世界,首先需要对何谓“现象”展开对话;要进入量子力学的世界,对量子思维在各学科之间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转化,则要以对什么是“量子”的理解与把握为前提。同理,“教育”作为公共概念,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视域中的教育,数学、物理学、化学和新兴的智能科学、数字生物学视野下的教育,呈现出各学科的立场及其内隐的视角与眼光,它们以“教育”为汇聚点,通过己方和他方观点的涌现与碰撞,一场场跨学科对话的进程得以持续发生,促使人类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愈加丰富起来,最终推进人类教育知识的增长与进步。
正是因为概念里有如此丰富的意蕴,所以才使得“概念研究”的意义非凡:以概念建构与创造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并创造新的理论范式,甚至创生新的科学样式或学科。例如,“智能科学”“智能教育学”,就是以“智能”概念为起点与推动力建构而来的新兴交叉学科。
三、如何推动“概念研究”?
既然概念研究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概念研究,充分发挥概念研究对于教育理论研究和它在教育学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一是更加关注思维方式。如前所述,概念和概念研究之所以成为学科发展、理论创新的原点,原因之一在于,它们蕴藏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尤其是思维方式,它与价值观一样,构成了学科与学术、理论与思想、概念研究与概念体系重构的原点。换言之,重构概念,需要重构思维方式;重构教育学的概念体系,则需要重构教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在跨学科的意义上,“量子思维”可以成为教育学思维转型与重构的方向与目标之一。从这个角度看,跨学科研究,就是跨学科思维。相关学科或者异域学科的概念的引入,牵动的不只是概念的改变与丰富,还有思维的改变与拓展。
二是更加关注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当今,以智能科学、脑科学、量子力学、合成生物学或数字生物学、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等为标志的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涌现,为教育学的概念研究和概念体系重构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带动对“人”“能力”“素养”“学校”“学习”“教师”“学生”和“教育”的创新性甚至倾覆性的理解。如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数字生物学等共同催动生成的“数字虚拟人”“人机合成人”“硅基人”,以及“虚拟教师”“虚拟同学”等,颠覆了传统的人性观和传统的教师与学生内涵。这些新学科的出现,既意味着更多新概念出现了,还意味着老概念可能会有新界定、新内涵,新老概念的交融共生,有可能带来教育学概念体系的大变革,为教育学和中国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构筑新的概念基石。
三是更加关注融通转化。17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用过一个美妙的比喻来表示自然认识的不同途径,分别是“蚂蚁式”“蜘蛛式”和“蜜蜂式”。他认为:“我们不能像蚂蚁那样只是耐心地收集材料——这是经验主义的做法,它不能使我们走远;也不应像蜘蛛那样只顾自己吐丝织网——这是理智主义的做法,也不会达到目标;而须像蜜蜂那样从花中吮吸花蜜,并且在蜂巢中加工成蜂蜜。单纯收集事实,或者仅有概念框架,都还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使两者形成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科恩,2020,第40页)。显然,在培根眼中,观察者只是像蚂蚁一样收集知识碎片,而没有把它们加工成某种坚实、可靠和系统的东西。自然知识的收集与整理,必须以蜜蜂为榜样系统地进行。培根为此呼吁建立有组织的研究群体,按照一定的方法对材料进行加工,以这种方式得到的蜂蜜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蜜蜂式的认识方式、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实质就是“融通转化”,是不同材料、不同事实、不同路径、不同方法之间的相互融通、交互转化。对于概念研究而言,既有同一概念的历史性、现实性与未来性的融通转化,将过往活在当下,并赋予历史与现实新的未来;也有中国教育学与世界教育学概念体系的融通转化,核心要义在于概念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力求“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眺望世界”;更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概念体系的融通,既立足教育学立场,又跨越教育学、超越教育学的边界,以跨界思维、超限思维建构教育学的概念体系;还有基于概念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融通转化等。
四是更加关注贡献能力。无论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学人,学术尊严与学术地位的高低,取决于是否具有概念贡献能力,即“概念贡献力”的程度。这种贡献能力至少有两个类型:一是概念辨析的能力,善于进行概念的界定、解释与厘清;二是概念建构或概念构造的能力,朝向于概念创生,其中既有“赋予老概念以新内涵”,如叶澜对于教育的重新界定——“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也有“提出新概念”,如薛定谔提出“量子纠缠”等。在更深层次上,概念贡献力的实质,是“知识贡献力”:凭借概念重构与更新,推动新知识的产生。由此,再次展现了概念研究的重要性:通向知识再生产,成为知识生产力、知识贡献力的源泉。而知识贡献的能力,来自于概念界定力、解释力、厘清力和构造力。
五是更加关注概念误区。越是推崇概念和概念研究的重要性,越要警惕概念的误区,保持一份在概念面前的清醒与理性,尽可能减少概念探险中的概念历险和概念风险,走出概念的丛林和概念的误区(石中英,2019)。首先,清醒于概念的限度及适用范围,正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一样,也没有适用于所有语境的概念。每个概念及其内涵都有特有的边界,所谓的概念“界定”之“界”,就是“边界”“界域”。界定了一个概念的内涵,就确定了一个概念的边界和领域,一旦超出原有的界域,原概念就失效。耶林认为,“概念法学”可能带来的误区在于,它“不考虑法律在实践中的最终目的和适用条件,而仅仅在其中看到了唯一的一个对象,并用它来测试那随心所欲、自带魅力和自成目的的逻辑思维” (耶林,2023,第37页)。其次,清醒于概念与真实、日常生活之间的割裂。由于概念是抽象而来的,而且主要是对生活经验和体验的抽象,抽象之后的概念往往已不复生活的原样。当以一个概念为视角审视生活之时,生活就被概念化了,很容易远离或背离具体而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一定是具体的、鲜活的。这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概念不能不抽象,但抽象必然带来对具体生活的远离,而当概念回到生活之时,可能会出现不适用或不合理的问题。如同耶林所言:“只关注由概念组成的或由概念的演绎得出的法律规则是否符合逻辑,而不考虑由概念组成的或由概念的演绎得出的法律规则是否符合逻辑,而不考虑规则在生活中能否适用或适用后的结果是否合理”(耶林,2023,第37页)。再次,清醒于概念与教育实践的分离。与概念和生活的割裂一样,教育学的各种概念及其开展的概念活动,形成的概念事件,本质上是理论活动、理论事件,依循的是理论逻辑,或多或少带有先验性、演绎性,因而存在着与生活逻辑、实践逻辑分离、割裂的风险。如何避免基于先验演绎的理论体系而来的“概念先验主义”,避免那种以逻辑为唯一要素,但没有任何实践要素的概念建构和概念体系建构,转而让概念生活化、实践化,让概念活起来,变成活泼的概念,这是教育学体系重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无论如何,如下提醒理应贯穿渗透在教育学概念基石构筑与概念体系重构的全过程:当我们在概念天国里尽情遨游的时候,不能忘了生活的大地和实践的大地。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07月31日发布文章,作者李政涛,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原标题:《【关注】李政涛:概念研究为什么重要?——构筑教育学建设与发展的概念基石》


